“马魂、中体、西用”论强化民族文化主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界对“马魂、中体、西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您提出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比如“马学为魂”之“马”是指什么,“中学为体”与清末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又有什么区别?
方克立:“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句话讲的是马、中、西三“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马学为魂”之“马”,首先是指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指坚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本质的东西,最具有“灵魂”意义的东西。有人把“马学为魂”之“马”曲解为某种具体的学说或某个人的思想,那不是我的观点。
我说的“中学为体”之“体”,不是“道体器用”之“体”,而是“器体道用”之体,不是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而是作为文化发展载体之“体”,讲的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就与清末张之洞等人以孔孟之道和“中国之伦常名教”为“体”的观点鲜明地区别开来了。我用“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集中阐明和论证“中学”(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尤其是“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它不仅是对西学而言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而言的。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如果不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再好的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任何作用,不但不能起“他山之石”作用,更不可能起到引领时代思潮的指导思想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化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西学为用”的意义比较明确。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讲了两个“服务”,而我也讲到过“西学为用”的两重含义,指出它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说,它有“道体器用”之“用”与“器体道用”之“用”两重意义。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范式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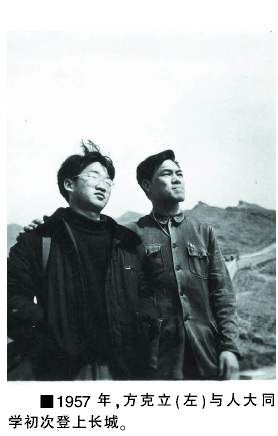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问题意识很明确,就是力图正确解决文化综合创新中的中、西、马关系问题。这里的一个难点是需要突破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而代之。已有学者指出这得益于您长期关注体用范畴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理论价值和内在限制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才能根据现实需要与理论逻辑提出新的思想范式。请您介绍一下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方克立:我在1984年发表了《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对体用范畴的多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作了一些考察。1987年写的《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哲学研究》第9期)一文,已把注意力集中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指出争论双方使用的体用范畴含义并不一致,因此就没有实质上的针对性。比如,晚清张之洞等人所讲的“中体西用”,“体”是指万世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用”是把原则“举而措之天下”即运用于具体实践,这是一种“道体器用”的观点。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则是以包括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在内的社会存在为“体”,而以“西体”运用于中国、取得“中国化”的形式为“用”,这显然已回到崔憬、王船山等人的“器体道用”论。
张岱年先生对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他意识到分歧正是在于对体用范畴的含义理解不同,但他还是试图把中、西、马三“学”放在体用二元模式中来说明,因此有些关系难以讲清楚。比如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话中,他把中华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主义指导原则都放在“体”的地位,而科学技术等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其实两个“体”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道体器用”之“体”即主导性之“体”,另一个是“器体道用”之“体”即主体性之“体”,他没有把二者适当区分开。我曾经讲过,张先生的这个表述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我是在他上述思想辨析的基础上,引进“魂”这个概念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之“体”,而用“体”这个概念专指作为文化发展载体的主体性之“体”。把两个不同含义之“体”区分开来,运用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就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魂”)与中国文化主体性(“体”)摆在既有区别又有机统一的关系中了,而处理好这个关系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化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