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翻译中语言和概念最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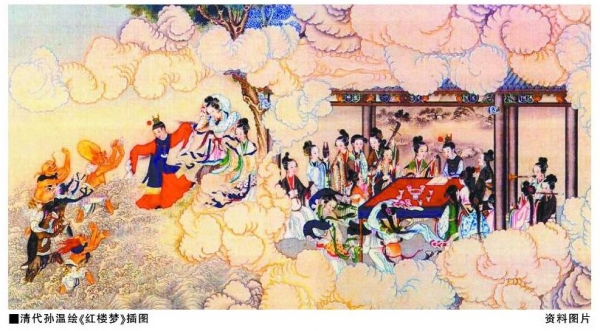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下您主持的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名著翻译工程?目前进度如何,遇到哪些困难?
浦安迪:目前我主持的一项中国古代思想名著全集的翻译工程,计划出四五十册,主要书目是中国先秦至唐代的思想经典,如《法言》、《左传》、《说苑》、《竹书纪年》、《晏子》等五十册,当然也包括《史通》,形式是中英文对照。《论语》、《诗经》有翻译的计划,但还未着手,译者以海外学者为主。第一批著作将会在几个月后出版,包括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翻译的《法言》、李惠仪和另外两位学者翻译的《左传》等。这并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计划,我们鼓励一些学者提出申请,然后我们来批准。
这个项目始于十几年前,先是同耶鲁大学合作,后来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由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想法是,在海外汉学界,虽然汉学家能够阅读汉语原文的著作,但是有的学生尚力有未逮。给学生上课还是需要翻译本。19世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经翻译过部分著作,但是当时的英语很难读,而且每一部都是按照当时最流行的程朱评注的方法,并没有把不同的见解调和,这次的《左传》由三个人合作,以李惠仪为主,翻译很精良。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四书已经出版。
当然,做这个项目有一些困难:一是语言,二是概念。翻译古代思想文献,首先要明白作者说了什么,但是很多文献很难理解,需要依靠古代的评注。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位对您影响很深的老师?
浦安迪:我会提到牟复礼先生。他于1922年生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很小的村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金陵大学学习文史。1956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东亚学系,一直到1987年退休。30年间都没有做过系主任。退休之后,牟复礼先生移居科罗拉多的山中,实现了山居的理想。
牟复礼先生著作等身,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汉学家的研究领域竟能如此广阔。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明初诗人高启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诗歌,而且将其作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考察。他的《中国思想之渊源》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文化最基础的东西,被很多美国大学的汉学系作为教材,其中内容非常深刻。后来他还翻译了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在1979年出版。除此之外,他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撰者,1988年他和杜希德出版了头两册,影响很大。最后是《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中国通史虽然有好几个版本,但是这本书是很特殊的,此书出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读完了1000多页,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和新的启发。
链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评点浦安迪:
浦安迪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学者,也是一位很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经典有着深入了解的汉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小说,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也有着贯通性的深刻理解。
浦安迪懂得很多种语言,至少是美国汉学家中懂得外语最多的人。而他又有很强的犹太文化背景,是犹太宗教的忠实实践者。他从前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其背景是明末文化,当时他就很重视经典当中体现的文化价值、道德意识。后来,他的学术生涯出现了转型——从古典文学转向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表面上看,这两个领域差别很大,但实际上有相通之处。从研究小说的方法来看,他并没有把其作为纯文学,而是将其视为“新经典”。所谓“新经典”,就是认为明清小说,特别是明末小说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小说本身,而是通过注解体现出来。浦安迪将小说和评论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要理解小说的底蕴和内涵,不能脱离后人对它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小说看成儒家经典的经和注,而后来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反过来影响了其小说研究。另外,他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本中的“修辞”,比如儒家经典的经和注存在一种“修辞”关系。这里的“修辞”指一种表达,对经典含义的阐发,带有诠释学的意味。
因此,浦安迪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儒家经典研究以及犹太经典研究可以看作是互通的。这是他研究的另一特点。一方面,他能像文学批评家一样从文本内部考察它的结构;另一方面,也能越出这个范围,从明代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观察。后来,“新批评”也影响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既有着原来特殊的学术风气训练下的学术倾向,也结合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发展出对经典独特的阅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