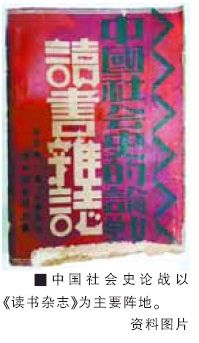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多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学术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我就不多说了。但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始于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和刊物大量出现。众所周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杨匏安、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先进分子,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人统计,在1925—1927年间,仅上海出版的马恩著作、专题文集等,就达50多种,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外,另如中华革命党主办的《建设》杂志等,也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都在《建设》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这说明,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欧美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而加以认真对待,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或启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潮流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产生的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说所凸显的理论优势等,是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必须要了解的前提条件。如果翻看《毛泽东选集》,会发现开卷两篇都是讲中国社会的,都采取了经济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都涉及社会性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所以,不了解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同样不能深刻认识何以会出现大论战。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是不是实践上、理论上都出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倒逼着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思考的逻辑秩序,是落到社会性质上来。只有弄清楚社会性质,才能确定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步骤与方法等。所以,寻求这些问题答案的急迫性非但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减缓,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人们面前。
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共产国际的总部莫斯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布哈林认为,中国军阀代表的封建残余势力占优势,中国革命应该以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结合为主。而托洛茨基、拉狄克主张,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的国家,革命目标应在反帝反封建之外,再加上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显然,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其一贯主张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应用。莫斯科出现两种声音,无疑会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回响。这段历史会让我们体认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路,走得多么不容易。还是那句老话,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这真是一条真理。这里,我就不复述历史的细节了,但要指出,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都圆满地解决了。毛泽东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和革命不断论者的结合者。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社会性质的判断与认识的正确。
还需要说明的是,除中国共产党人外,参加社会史论战的其他各派别,也受到莫斯科争论的影响,而且影响都很大。因此,走得越近越会发现,论战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和繁乱。